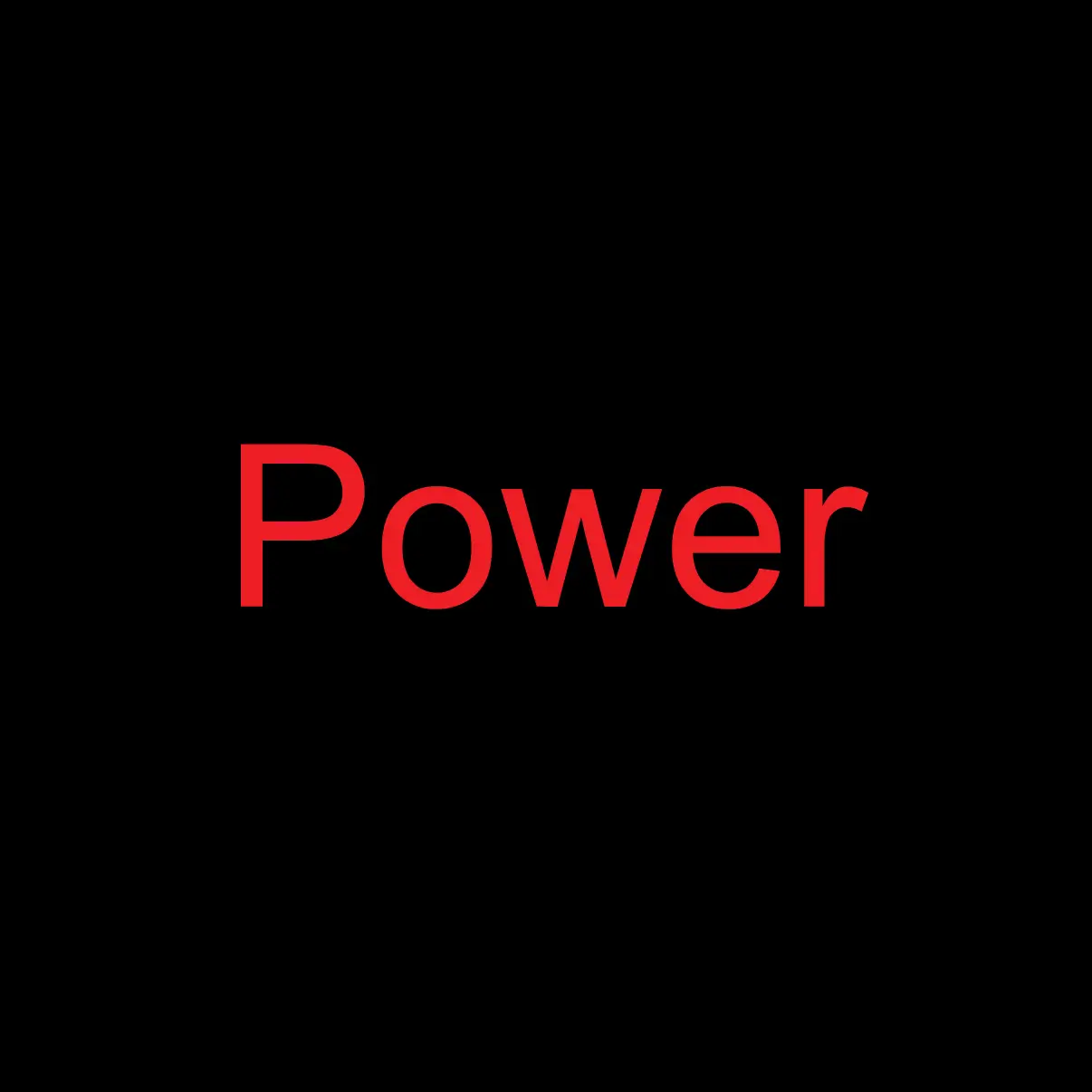基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暴行与否认审视《代顿协议》
国际法研究与政策中心办公室,佛罗伦萨,2025年2月14日
2024年“和平调解与法律”专家会议 |《和平谈判中的法律》第二版 |与伊沃·约西波维奇阁下的CILRAP对话 | 与伯特兰·拉姆查兰博士的CILRAP对话 | 与达格·尼兰德大使的CILRAP对话 | 与约翰·维贝大使的CILRAP对话 | 2007年研讨会及政策简报 | 莫腾·伯格斯莫撰写的第149号政策简报系列
在《代顿协议》签署30周年前几个月,此次闭门会议在佛罗伦萨的CILRAP 办公室举行,会议结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暴行及其否认问题对协议进行了审视,重点关注协议是否最终以牺牲积极和平为代价,变相奖励了核心国际罪行。会议由CILRAP主任莫滕·贝格斯莫主持,与会者包括伊沃·约西波维奇教授(克罗地亚前总统)、刘大群法官(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法官)、埃尔林·霍姆副大使(挪威驻罗马大使馆)、萨拉·钮文教授(欧洲大学学院和剑桥大学)以及彼得·麦克洛斯基先生(前国际刑事法庭前南斯拉夫问题检察官,负责斯雷布雷尼察案件)。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平总框架协议》及其11个附件(包含10项协议和一部宪法)于1995年12月14日在巴黎签署,目前仍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克罗地亚以及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简称“南联盟”,后为塞尔维亚)三方之间有效。该协议的主要成就包括:(一)在波黑及三方之间维持了近30年的和平;(二)确保了波黑与南联盟之间的相互承认;(三)在波黑建立了宪政体制;以及(四)为受武装冲突影响最严重的波黑提供了国际援助、合作与贸易的条件。这些成就是30周年纪念时应予回顾的重要内容。《代顿协议》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简称“ICFY”)主导的三年进程接近尾声时达成的。在其CILRAP对话中,ICFY主任伯特兰·拉姆查兰博士讨论并捍卫了《代顿协议》及ICFY的工作。
然而,《代顿协议》的实施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在波黑,其中由《代顿协议》分权政治体系所承认的实体“塞族共和国”使宪法机构陷入瘫痪,并多次威胁要从波黑分离出去。因此,《代顿协议》受到以下批评并不令人意外:(一)创建了一个复杂的治理体系,导致实体层面与国家层面之间容易陷入僵局;(二)助长了对国外或国际行为体的依赖,这些行为体将资源输送到非政府组织,却牺牲了本地行为体和经济投资;(三)虽然结束了战争暴力,却创造了一种“消极和平”,将波斯尼亚穆斯林与塞族之间的分裂制度化;(四)未能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真正和解;以及(五)未能充分培育共同的波黑认同,而是按照民族主义身份分配权力。要回应这些批评,需要对波黑的局势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而相关作者可能并不总是具备这些条件。
此次在佛罗伦萨CILRAP 办公室举行的闭门会议探讨了《代顿协议》的成就及其面临的挑战。会议从1992年至1995年间在波黑发生的严重核心国际罪行的角度,深入审视了《代顿协议》,旨在评估其是否为未来的和平调解提供了可能的经验教训。尽管《总框架协议》第九条承认各方有义务“在调查和起诉战争罪行及其他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方面进行合作”,且协议的实施为前南斯拉夫问题法庭(ICTY)在波黑进行前所未有的调查和逮捕提供了便利,但《代顿协议》也因承认在前三年半期间犯下严重国际罪行的“塞族共和国”,赋予其合法性和重要的宪法权力而受到批评。“塞族共和国”被排除在直接参与代顿谈判之外(取而代之的是南联盟和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先生作为其代表),且波斯尼亚塞族领导层并未获得对核心国际罪行的豁免权——相反,高层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奇、拉特科·姆拉迪奇、莫姆契洛·克拉伊什尼克和比利亚娜·普拉夫希奇均被ICTY审判。然而,《代顿协议》使通过他们的罪行诞生的“小国”成为法律现实,并在宪法上确认了其自1992年春季以来通过攻击(包括灭绝行为)和强行驱逐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所夺取的大部分领土。更令人痛心的是,后来的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普遍否认波斯尼亚塞族和塞族军队所犯下的暴行(这一点已被ICTY、波黑国家法院和克罗地亚法院的众多判决所证实,包括与斯雷布雷尼察相关的种族灭绝定罪)。
《代顿协议》赋予波斯尼亚塞族的社会政治利益,和他们为建立和巩固“塞族共和国”所采取的手段,这两者之间的脱节引发了一些问题。在斯雷布雷尼察7000多名波斯尼亚穆斯林非战斗人员被大规模杀害仅几周后达成的《代顿协议》,是否通过巩固“种族清洗”违反了“非法行为不产生权利”(ex injuria jus non oritur)的原则(赫希·劳特派特称之为“一项确立已久的法律原则”)?这一原则如何适用于和平调解?它是和平与和解进程的指导原则,还是不应限制外交手段?是否有必要在《代顿协议》中赋予“塞族共和国”实体地位?在克罗地亚的“风暴行动”(持续至1995年8月14日)、北约的“审慎力量行动”(持续至1995年9月20日)、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克族部队的“梅斯特拉尔2号行动”(持续至1995年9月15日)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军队的“萨纳行动”(结束于1995年10月20日)之后,波斯尼亚塞族的军事实力是否强大到足以证明调解方将“塞族共和国”合法化的合理性?这是一个有趣的事实问题:在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如纸牌屋般崩溃的同时,参与代顿进程的行为体是否曾告知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克族军队不要夺取普里耶多尔(波黑一些最严重罪行发生地)或巴尼亚卢卡?如果是这样,原因是什么?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我们能否为未来的和平调解得出一些普遍性的见解?